散工属于什么职业(做散工职业如何填写)

漱石杀死了一只猫
约翰·惠蒂尔·特雷特 / 文
王立秋 / 译
尽管漱石本人经常要求美国学生阅读他1914年的小说《心》的,但事实上,夏目漱石最“正典的”作品,是《我是猫》(1905—1906)。这可能是一个古怪的选择。《心》的译者埃德温·麦克莱伦(Edwin McClellan)认为《我是猫》并非严肃的文学作品。在日本,文学史家伊藤整(Itō Sei)认为它肤浅而充满了失败的、风趣的尝试(失敗為る駄洒落)。另一位权威,山本健吉(Yamamoto Kenkichi)则说它不但奇怪(風変わり),而且是“一个在日本文学史上没有先例,也不曾再次发生过的古怪的错误”。尽管如此,它依然是漱石第一本畅销书。她的妻子记述说,这本书赚的钱足够她大买一波帽子了。事实上,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一位日本学者说的那样,《我是猫》还变成了“我国の国民文学作品”(“我们国家的国民文学作品”)。中学的孩子都要读它,一位学者还称《我是猫》在各种媒体上的衍生作品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学史的档案馆。正如小森阳一(Komori Yōichi)所说的那样,“人人都知道它”。
但它在漱石文集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反常的。由一只猫来叙事;书中,除了一些模糊的人类关于一场婚姻的闲谈外,没有发生更多的事情;对于书中的主要人类角色苦沙弥教授,作者也没有进行什么有技巧的刻画——这部小说当然会被甚至更多的批评家认为是一个失败了。在出版的时候,它就遭到了批评家的冷遇。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吉本隆昭(Yoshimoto Takaaki)虽然承认它在当时是热门著作,到今天也依然广为人知,但他也批评其内容不都是那么有趣,并怀疑许多读者甚至都没有把它读完。它属于漱石职业生涯早期的“幽默阶段”,漱石本人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称之为讽刺(風刺)。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关于1904—1905年俄日战争(在第五章中,这只猫和老鼠打了一架)的复写,但这点是很难看出来的;战争也不易取笑。它还被斥为漱石写的唯一一部搞笑(面白い,滑稽)作品。记者长谷川如是闲(Hasegawa Nyozekan)认为,《我是猫》向日本明治时期之前的过去倒退了半个世纪。如果你把《我是猫》当作对漱石及其自负的明治后期知识分子的嘲讽来阅读,那么你会发现,在被选入学校教学大纲的作品经常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释的现代性的国民经验方面,它什么也没说。为什么《我是猫》虽然怪异,却依然是一部对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学史来说如此重要的作品?这就是我在本文中提出的问题。
《我是猫》通篇是由一只属于苦沙弥(“嚏”)教授的家猫来叙述的,而使它成为一部经久不衰之名作的,正是这只猫对人类——特别是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讽刺评论。它的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治时期的演说的创新。“演说”是福泽谕吉的发明,他从1874年开始提倡演说,以之为启蒙蒙昧者的手段。《我是猫》也让人想起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言事前使用冒昧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我輩”,和在句末使用同样傲慢的连系动词であるんである(就是这样)的爱好。漱石对演说的讥讽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到小说结尾的时候,当这只无名的猫-叙事者掉进桶里淹死的时候,《我是猫》读起来不仅是对明治时期的社会风俗,也是对当代媒体之刺耳杂音的大规模的、曲折的、引人发笑的和学究式的滑稽模仿。1905年,漱石正在写作某种不太像散文、不太像俳諧、也不太像文的东西。就像他的诠释者之一,柄谷行人(Kōjin Karatani)所说的那样,他逆时代的潮流而动。《我是猫》是各种写作风格和话语的大杂烩,在柄谷所谓的“狂欢荒诞”(carnivalesque)中达到顶点,它很难说对当时的现代日本文学作出了什么贡献,也算不上是与之分歧的宣言。但在见证漱石成功的时候,柄谷也同意,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把《我是猫》当作讽刺作品来阅读。
和漱石后来那些精心雕琢的小说不一样,《我是猫》——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意在取悦朋友的短篇小说——并没有什么情节结构或角色的发展。用漱石自己的话和那些他也曾用来描述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的话来说,它写得“无头无尾,是一个像海蛞蝓一样的造物”。之所以会这样,一部分原因肯定在于,漱石是用过去的德川文化(他本人就是在这个文化中长大的)和现代性给日本带来的新东西(他注意到了这些东西,但他并不特别迷恋它们),来建构他的小说的——《我是猫》叙事的抑扬顿挫和它的轶事风格也让人想起传统的“讲故事”。“在他写故事的过程中,”一位日本文化史家这样写道,“我们可以看到,他无意识地把握到了媒体与人的关系。”许多批评家依然没有看到这个把握,甚至在他们为证明《我是猫》属于对文学和国民历史来说漱石所代表的的那个东西——日本——而研读其文本的时候,也没注意到这点。
漱石依然是日本断断续续之现代性的古怪的——但又是完全适当的——象征。正如小说家水村美苗(Mizumura Minae,1951— )在谈论他的时候说的那样,“在民族语言形成的时候,就会魔法般地出现一个国民人物,他一人就体现了历史的过程。”如果说苦沙弥教授为他所在的资产阶级世界深感泄气的话,那么这可能是因为,就像历史学家奈地田哲夫(Tetsuo Najita)所说的那样,“漱石,在反思日本的现代化的时候,并没有把它看作人类之期望的实现——其中,现代的人比他古代的祖先更幸福——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向全面的精神衰弱挺进的残酷剥削。”漱石通过写作一系列这样的小说来表达自己的犬儒:这些小说只有一部是自传性质的,但它们都取材自跟他的社会和智识同伴的经验相近的经验。他1908年的《野分》(秋风)开头第一句话是这样的,“白井道是个文人(文学者)”,意思是,白井是个教师、作家和传道者——但考虑到漱石所理解的现代日本对它的知识界是冷漠的,他首先是一个失败。这样的小说能流行,这个事实,可能就像杰·鲁宾(Jay Rubin)所说的那样,与“[漱石]用来传达其世界观的不可磨灭的意象”有关,但在这里,这位日本公认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何以以及为什么会在坚定地批判的同时这么干,也是个问题。
漱石的讽刺很少被诠释为意识形态的。尽管他公开采取的立场可能也有意识形态的意味——比如说,拒绝文化教育部授予的文学博士,或抗议政府设立官方的文学委员会——但据说,漱石做这些事情,乃是出于个人的正直,而没有什么政治的意图。漱石无疑被其时代的极端爱国主义给激怒了(就像他也被许多事情激怒那样)。众所周知,在他的演说《我的个人主义》(私の個人主義,1914)中,他嘲弄了那些打着爱国旗号来卖自己的豆腐的日本公民(豆腐屋が豆腐を売ってあるくのは、けっして国家のために売って歩くのではない)。在这方面,加藤周一(Shūichi Katō)的陈词滥调也有一定道理,他说,森鸥外与政权合作,内村鑑三(Uchimura Kanzō)批判政权,永井荷风逃避政权,而“夏目漱石则是把政权最小化了”。但如果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本身就是要显得最小化的话,那么漱石和他尖酸刻薄的讽刺看起来就有点跟不上节奏了。讽刺,尽管经常被引述为颠覆性的,但其实和在西方一样,也是日本现代性的一部分,只不过在西方那里,现代主义的讽刺和对权力问题的冷漠之间的共谋也广为人们所注意。在思考漱石的时候,我们也要记住,他的小说经常是从日本的统治精英外部,但同时也是从日本国民内部向我们说话的。
尽管没完没了的批评著作意图证明漱石作品的一切特征和轮廓都可以追溯到他自己的病态的自在(ill-ease)(甚至是病/不自在[dis-ease]),但现代性也意味着一种从公共到私人的移动这个事实,可能也意味着对桀骜不驯的漱石的恋物式崇拜也许是一种掩饰——也许,把它底下的东西当作意识形态的作品来思考会更合适。1905年,日后将让漱石暴怒的自然主义几乎还不存在,但自然主义这个说法是有的,且漱石已经在与之作战了。和岛崎藤村(Shimazaki Tōson)《破戒》(1906)的叙事者(在岛崎那里,叙事者没入了主角)不一样,漱石的叙事者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一直不完全地投身于自己的故事。他是怎样做到这点的?柄谷会说:通过抵抗二叶亭四迷为日本虚构作品开创的叙事的过去时,并因而“抵抗现代虚构作品的叙事模式”。《我是猫》和漱石早期的其他作品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同寻常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且经常是用非过去时态来叙事的。但漱石的《我是猫》并不是只和某种抵抗有关,无论我们有多希望是这样。漱石坚持在20世纪写作在当时已经是矫揉造作的滑稽本、読本、俳谐和汉诗——柄谷写到,这些文体的灭绝“就是现代文学的诞生”——靠的就是那种伟大的、反生产的讽刺。
樋口一叶不是唯一一个被今天日本银行发行的纸币纪念的贫穷的现代作家。更为新近的一件与漱石相关的充满讽刺意味的事情是,漱石的脸被印到了日本政府于1984年发行的千元日元纸币上,尽管漱石本人并不欣赏政府给予知识分子的荣誉,并且总的来说,他也对金钱不耐烦。《我是猫》和漱石的许多小说一样,也被认为对现代性抱有敌意,因为作者厌烦财富,而后者又是他所没有的东西。(苦沙弥的姓氏“金田”意思就是“金钱的田野”。)但在现代文学中,又有哪部作品曾明确地拥抱过财富这个东西呢?漱石珍视隐私,并使隐私成为日本文学现代性之物,可他的脸却作为国家货币上的圣像四处流通。但这里可能存在勾结而非冒犯吗?阿兰·图海纳认为,“现代性的历史,就是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行动者浮现的历史,他们”和漱石一样“逐渐地失去了他们对现代性是好的第一个具体定义的信念”。但漱石的敏锐的读者江藤淳(Etō Jun)则断言,与对抗相反,“漱石把明治时期的民族国家当作他自己的国家”。谁是对的?
《我是猫》原本不过是它现有文本的第一章。它是1904年初漱石为诵读以取悦山峡朗诵会的其他成员而快速写出的。山峡朗诵会是由围绕高浜虚子(Takahama Kyoshi,1874—1959)这个核心人物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学士组成的一个小团体,高滨虚子曾断定,有山或顶峰的散文是糟糕的散文。虚子是这样回忆漱石阅读其文章的那个日子的:“它是如此地不同于我在山峡读书会听过的一切,以至于我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它,但它是如此地幽默,我真的很喜欢它……我把它放到了《杜鹃》次年的1月号上。它让他一夜成名了。”环境是“壮言大语の句会”,一种“壮言大语的朗诵会”,这在当时是一种流行的消遣活动,《我是猫》里的青年诗人东风君就提到过这样的朗诵会,根据高桥康雄(Takahashi Yasuo)的说法,它是“印刷文化时代声音文化”的残余。这样的朗诵会今天也有,不过只是为诗歌而设的。口头发表的散文被留给了广播、光盘、播客和其他数字媒体。《我是猫》的开头几页是用诗律写成的:它是为在山峡朗诵会上诵读而设计的,在会上,漱石是噺家(讲故事的人),而其他作家则是他的听众——我们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我是猫》的表演性质。演说及其与写作的不谐是漱石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个主题,而对于《我是猫》之于日本文学史的意义来说,山峡朗诵会的戏剧性是很重要的。但在1904年的东京,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戏剧性在其他地方也很重要。
经常被称为鹿鸣馆时代的1880年代中期是日本改革热情的巅峰。改良是一种看起来可以应用于一切(包括戏剧)的风尚。1886年夏天,刚从英国回来的末松謙澄(首相伊藤博文的女婿)成立了戏剧改良会。伊藤也是创始成员之一,其他创始成员还包括井上馨、穂积陈重、外山正一和福地桜痴(福地源一郎)。从一开始,戏剧就意味着歌舞伎,是年10月,末松在一次演说中概述了改革歌舞伎的十大目标,其中就包括政府对版权和表演权的管理。他的改革并非都取得了成功,但政府管理这一点是成了。从一开始,来自现代戏剧的重要声音,比如说森欧外和坪内逍遥(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凯撒》是用净琉璃的音律风格创作的),是反对协会社会的,他们认为这个协会不明智地对艺术家设限。遭到质疑的是艺术家与政府之间的共谋可以生产出有意义的文化这个想法,但政权心里想的恰好就是这个。尾崎秀树指出,一段时间后,甚至浪曲(rokyoku)和回顾谈(kodan)也开始“散发出国威的臭气”。
戏剧改良会的最大成就,是正式恢复了歌舞伎:1887年,天皇第一次来看了歌舞伎。正如爱德华·塞登斯迪克所说的那样,这个半官方的天览(tenran)在明治时期还发生过许多次,它给了歌舞伎“究极的声望”。九代目市川团十郎、五代目尾上菊五郎和市川左团次在贡院在天皇、贵族、高官和精英协会的成员(若非如此,这些人绝无可能在实际的剧场中立足)面前演出。演员们没演庸俗的世话物,而只是舞蹈和一出基于极其体面的能剧《安宅》的历史剧《劝进帐》散工属于什么职业,由三代目並木五瓶出演。这次天览的意图是给按模型改革的歌舞伎,即一种无当代指涉的歌舞伎以官方的肯定。这也是从1876年天览能剧开始的激励无精打采的古典戏剧复兴,使表演成为新形成的民族-国家一部分的那个举动的一部分。十年后,即将大量承担民族主义教育任务的回顾谈也得到了天览。
讽刺的是,天皇对歌舞伎(和对其他表演艺术一样)的支持,实际上意味着当时意境没有进一步改革歌舞伎的迫切需要了。如今,它的古典形式变成了民族遗产的一部分。戏剧改良社遭遇了与伊藤政府相同的命运,但歌舞伎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许可。一旦剧目被整顿,德川时代歌舞伎的首要功能之一——也即传播当前发生的事件——也就被消除了。兴津要(Okitsu Kaname),尽管对明治早期的文学心怀成见,但他却正确地指出,日本小说史在走向现代的时候是包含它与戏剧的关系的。如果说现代英文小说部分地是从叙事歌演化出来的话,那么日文小说就是从舞台演化出来的。但一般来说,戏剧并不包括作为回顾谈和落语的寄席演芸。落语,被翻译为“公开讲故事”,被定义为“一个简短的、以点睛之笔作结的滑稽故事”。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太过于粗鲁,以至于算不上文学。在落语那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想到现代文学的东西:它没有只顾自己的叙事者,也没有痛苦的多余的人。事实上,它有的是现代文学的反面:它的叙事者绝非一个角色本身,而叙事者的故事则来自公共浴室、街道,甚至厕所,而绝不是它自己想出来的——当然,也不会来自大学。坪内逍遥在论证国剧之必要的时候,心里也没有想到更多的平民形式的寄席。不过,更大众化的戏剧形式,则可能受激励而按照文明开化的民族精神来改革自身。类似于歌舞杂耍的寄席是在18世纪末从大阪来到江户的,传统上,这个时间可以追溯到1798年,在大阪来的岡本万作开始在江户神田区一家草店开始表演的时候。安德鲁·马库斯在他关于德川时期的见世物的论文中说,它是从“市场和街巷里低下的叙事表演”演化而来的。杰拉尔德·费盖尔写道:“受欢迎的表演者和他们吸引的人群被迅速地移出开阔的街道(历史上革命行动发生的地方),放进被控制的结构经济。看起来,连用来指各种各样的厅堂的寄席这个词也很合适,它的意思是‘吸引群众之地’。”
结果,寄席屋的数量,在明治早期,在情感的公共表达的隔都化(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的第一阶段,有了爆炸性的增长。尽管政府措施的目标是抑制它们,但到1855年的时候,城里就已经有近四百个寄席屋了,而且入场费也不贵,到明治中期的时候也才三四钱。和第一章讨论的瓦版(kawaraban)一起,口头的表演,特别是回顾谈,是德川晚期传播时事新闻的主要手段,而国家也意图加以控制。在明治初期,所有形式的公共表演都还是被禁止的,原因显而易见。就像报纸报道的那样,任何集会都会因为ranbomono(乌合之众)的捣乱而被追究责任,任何群众的演说都是不可预期的。典型的德川末期的表演,森岡ハインツ(Heinz Morioka)和佐佐木美代子(Miyoko Sasaki)写道:“是一组把听他们的玩笑和恶作剧延伸到把既定的社会秩序也包含进去的角色。”还不只是玩笑和恶作剧:1867年夏天,当局还在寄席剧场上发现了爆炸物,这些爆炸物是一个会津藩的同情者(同时也是落语艺术家四代目可乐的岳父)放置在那里的。一个多世纪后,爱德华·福勒在他撰写的关于山谷地区(San’ya)寄席剧场的民族志中引用了一名散工的说法,这名散工告诉他“落语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抗议文学。多亏了落语,平民才能把他们对权威的抵抗说出来”。
但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情况还不是这样。当漱石另类地通过他的猫和苦沙弥教授来说话的时候,他和传统的落语的说故事的人(Rakugoka,落语家)很像,尽管和噺家(Hanashika,或咄家、话家)不一样,漱石应该没有在他的听众面前即兴表演。(虚子认为《我是猫》古怪,因为里面有猫,尽管许多落语里面也有动物。)据说,在这个时候,漱石对落语的热情最为高涨。水川隆夫(Mizukawa Takao)指出,他早在1904年就已经恢复去寄席的习惯了,而漱石的妻子镜子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肯定了这点。但漱石是听落语长大的,他儿时就去过日本桥的伊势本屋看过表演。不过,漱石在他的半自传作品《路边草》(Grass on the wayside,1915,这部作品描述了他在写《我是猫》那两年间的生活)中记录了一种对德川文化的纠结态度,这个态度有助于解释《我是猫》承担的意识形态工作。
到1877年的时候,东京的寄席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了。尽管最终回顾谈和落语有一定程度的复兴,但所有的寄席都对现代性做出了让步。落语即兴创作的能力变成了漫才的保留曲目,而今天,甚至在漫才那里,这个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失落了。在明治早年,二代目河竹新七也为了讨喜欢——也就是说,为求生——而放弃了他著名的白浪物(盗匪故事),改讲kaika kodan(“启蒙的历史故事”)散工属于什么职业,比如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故事。在1870年代中期的新闻潮期间,明治时期最反传统的表演者三遊亭圆朝(San’yutei Encho,1839—1900)会根据当天刊载的文章来表演落语。20世纪末东京日常生活的观察者井上純一(Inouye Jukichi)指出,寄席在当时依然非常重要。“这些地方对东京生活的影响不容忽视。的确,如今,报纸娱乐着整个社会;但当时的手艺人是从这些地方获得他所有的微薄知识的,而他对自己国家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和英雄人物的熟悉,也可以追溯到这同一个来源。就其教育影响而言,说故事的人这个职业很重要。”
1888年,天皇出席了桃川如燕的一次演出,后者的《猫怪传》(Hyakumyoden,百猫记)可能启发了漱石。圆朝声称,三年后,天皇也去看了落语,但官方的记录没有提到这个。和其他寄席不一样,落语最终决定保持“经典”(也即聚焦于关于爱情、父母与子女、妻子、盗匪、鬼、主仆、武士等的故事),但首先也要有一些创新。在漱石成长期间,他就住在寄席隔壁,对寄席极为熟悉。在《玻璃门内》(Garasudo no uchi,1915)中,他回忆了听到一个以他的军功故事而著称的说故事的人在隔壁侃侃而谈的情景。造访伊势本屋的经历意味着,他听过著名的回顾谈噺家,而且他一生都保持着去寄席剧场(次数或多或少)的习惯。在1888年给他的导师、诗人正冈子规(Masaoka Shiki,1867—1902)的一封信中(漱石与正冈子规的友谊部分地就建立在对寄席的共同爱好上),漱石写到了去看三遊亭圆遊表演,以及圆遊的表演是如此有趣,以至于他暂时忘记了他的慢性胃病的经历。
圆遊还以他的“すててこ踊り”(由穿短衬裤的男子表演的喜剧舞蹈)而著称,他最早表演这个节目是在1880年,在漱石青少年时,他的这个节目尤其受欢迎。《我是猫》后来也提到了这个舞。它倒不是圆遊原创的——和霹雳舞一样,它来自街头,据说源于吉原区,也可能源于静冈县。一天晚上,在浅草なみき亭的寄席剧场,圆遊突然从坐垫起身,掀起他的和服,然后把它塞进腰带。他露出大腿,踏出小腿,唱起一支自嘲的歌,并在跳着古怪的舞穿过舞台的时候假装要把自己著名的大鼻子撕下来——这一举动引起了观众震惊的掌声。兴津要认为这个事件是“新时代大众艺术的序幕”。在这之前,落语中的舞蹈还仅限于坐在舞台上晃动上身,兴津要说,なみき亭的观众为之而近乎于暴乱。圆遊在维新后的东京很受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都会跑过来看他表演。随后寄席接着又发生了其他充满活力的运动,比如说萬橘(圆遊的一个孙弟子)的hera-hera舞(the hera-hera dance),萬橘会半裸着跳这个舞。一些常去剧院的人想让警察来终结这样的闹剧,但圆遊和他的传人自然地用现代化的精神来捍卫他们的艺术。如果说圆朝使德川时期的落语趋向于完美的话,那么圆遊就是现代落语之父。
人们常说,落语中的此类闹剧是为了吸引新来东京的、不是很熟悉标准剧目的观众所需的,但也可能不只是这样。如果说明治时期从口头交流到书写文本的转变,是从声音到视觉空间的转变的话,那么这个转变是通过舞台来进行的。带着这样的后见之明来看,舞台上的身体运动是重要的——与其说是因为它严格意义上的在视觉上的新奇,不如说更多地是因为它降低了声音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它有意或无意地创造出一个前语言的(prelingual),因此也是前认知的(precognitive)直观性(immediacy,即时性、直接性)。鹤见俊辅(Tsurumi Shunsuke)写到,“姿势”是个人的和自发的,“像纸杯一样是一次性的”。瓦尔特·翁(Walter Ong)则持一种与漱石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尽管言词基于口头的言说,但书写却专横地把它们永远锁进一个视觉的场域。”有人指出,落语吸引漱石的地方包括它的kyodotaiteki na fun’iki,也就是说,它的集体的、公共的环境,在圆遊和三代目柳家小さん使落语变得越来越喜剧的时候,他们强调的就是落语的这个环境。圆遊的创新,如果确切来说还不是使落语现代化的话,那么它至少的确重新激活了落语,使它为新的观众所接受。兴津要说圆遊是“启蒙与文明的大众诗人”。但同时,另一位学者则指出,漱石偏爱落语而不是更现代的新派和回顾谈,因为在表演中,后者不如落语那么自然(这里说的看起来是自发性)。在漱石的小说《三四郎》(1908)中,一个角色评论说,他和小さ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多么幸运,而在自己的日记中,漱石也比较过他在肯辛顿看过的一场默剧和圆遊的表演。漱石自己的公开演说也不乏落语式的表演元素。当他在大学生面前发表他关于个人主义的演说的时候,他花了很长的篇幅来重述落语的“Meguro mackerel”(Meguro no sanma,目黑的秋刀鱼)的故事,把自己比作一条被剔去骨头的鱼,来为自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接受邀请来他们学校讲话而致歉。漱石对落语的迷恋在《我是猫》中就已经很明显了,他给苦沙弥的妻子安上了一个和圆遊一样大的鼻子。但在这中间又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使得这个关联变得复杂而不是那么地善意。
未完待续……
疫情严重,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跟家人:1.出门戴口罩;2.不去人多的场合;3.勤洗手、消毒;4.拒绝野味;5.如身体发生与感染此病毒相似的异常情况,请多加观察、及时就医;6.说服家人做到前面五条。关注最新的相关资讯,同时,也请大家不要污名化疫病、感染者、病源地和病源地的人,保持冷静和理智。如有余力,请通过确切、可信的渠道(注意:+已被列入失信名单)向疫区支援医护物资,并通过合宜的方式督促相关机构履职履责。愿所有人都安康,也希望生活跟工作尽早恢复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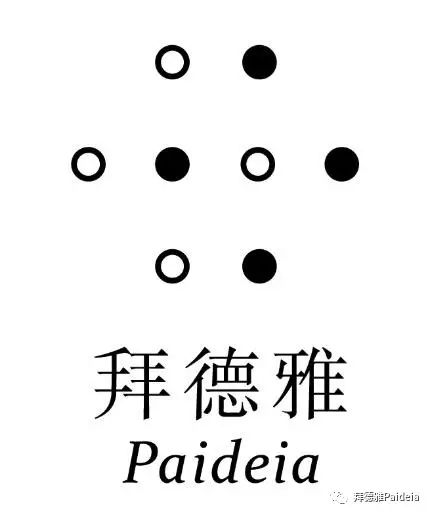
拜德雅(Paideia):思的虔诚
重庆 原样文化 出品

拜德雅Paideia





文章评论(0)